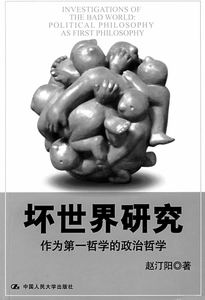 天下理念作为一种政治思维的意义大于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成就。实践总是不完美的,人性的局限足以破坏任何理想。但理想的意义不在于被实现,而是为了警告人类不能过分堕落。从理论上看,天下理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
天下理念作为一种政治思维的意义大于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成就。实践总是不完美的,人性的局限足以破坏任何理想。但理想的意义不在于被实现,而是为了警告人类不能过分堕落。从理论上看,天下理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
天下理论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是政治的最大情景或解释条件,因此包括了所有政治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够统一地思考所有政治问题,没有一个政治问题可以逃逸在外,因此,天下理论是充分有效的政治分析框架。在天下体系中,国家不是最大政治单位,在国家之上,还有天下(世界)。作为对比,在西方概念里,国家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只是个地理空间。无论城邦、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只有“国”而没有“世界”的理念,因此,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系列是不完全的,从个人、共同体而止步于国家,国家被当作是思考和衡量各种问题的根据或尺度。这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它缺少了世界这一必要的政治视界,因此无法表达所有政治问题。西方一直到现代才开始考虑比国家更广阔的政治问题,例如康德关于“人类所有民族的国家”或“世界共和国”的想象,但这一概念只被草草提及。康德认真的想象是“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仍然不准备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现在的联合国就是康德想象的一种实践。联合国不是世界政治单位,它并不拥有在国家之上的世界制度和权力,而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协商性机构,因此只不过是个从属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服务性机构。
天下概念创造了思考政治问题的“世界尺度”,它能够度量国家尺度所无法度量的世界性问题。按照天下理论,世界才是思考各种政治问题的总尺度,国家只是世界的从属性问题。虽然西方只有国家理论而几乎没有世界理论,但这不是说西方没有关于世界的思考,而是说,西方对世界的思考只是“以国家衡量世界”,国家的视界注定了在思考世界问题时总是仅仅考虑国家利益而无视世界利益,它看到的无非是“属于国家利益的世界”而没有看到“属于世界的利益”以及“属于世界利益的国家”,这样对世界不公。天下意味着比国更大的事情,因此只能以天下的尺度去衡量。天下理论试图“以世界衡量世界”,即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原理。“以天下观天下”的眼界显然比“以国观天下”的眼界更加广阔和更有责任感。很显然,并非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在“国”这个政治单位中被解释。有些事情是属于天下的,有些事情是属于国的,有些则属于家,如此等等。各个层次的事情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老子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管子也有类似说法:“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说法似乎早于老子)。老子这个原则意味着:(1)每个政治层次都有着不可还原的利益和权利;(2)不能以某个层次的利益去牺牲另一个层次的利益。既然世界存在,就必定存在不能还原为国家利益的世界利益。
天下体系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非常不同。“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显然,世界体系是由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互相合作形成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国家利益。世界体系或许有些类似中国所谓的“霸主”政治而不是天下政治。天下体系强调世界权力必须有利于世界公共利益,而不是掠夺世界,如荀子所言:“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天下政治的目标是使世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大到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破坏世界公共利益,因此达到世界的冲突最小化和合作最大化。
有效的政治体系需要所有政治层次之间的传递性或可贯通性,这就要求政治的各个层次的制度是同构同质的,从而保证政治秩序是可推广的。从逻辑结构上看,西方政治以个人为基本单位,从个人权利制度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国家主权制度,却无法推出世界制度,因此国家之治无法推出世界之治。天下体系以世界制度为准,下推国家,再推家族,即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天下――国――家”秩序,这样就能够保证政治秩序的普遍覆盖。墨子把这种政治传递性概况为“上同而不下比”原则,即下级政治以上级政治为准,从“一同乡之义,是以乡治”到“一同国之义,是以国治”到“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整个制度体系以“天下之义”作为最高保证。“天下――国――家”的推法虽然传递有效,但它只是单纯的政治有效性,而政治还必须能够普遍被接受才是充分有效的,否则有强加专制的可能,因此后世儒家试图完成“家――国――天下”的推法以保证天下体系的道德普遍有效性,从而形成“天下――国――家”的政治传递性和“家――国――天下”的道德传递性的双向传递,这样天下体系就具有圆满的内在循环。
但是“家――国――天下”的道德之推似乎不如“天下――国――家”的政治之推那么成功。儒家以亲亲为本而向外“推爱”至整个世界,这一推广必须经受“费孝通疑问”的挑战。按亲疏程度层层向外推爱(波纹同心圆结构)意味着关系越来越疏远,最后在陌生人那里消于无形。费孝通在《大学》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经典论述中解读出一个自私的逻辑:“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商鞅早有类似解读:“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儒家“道德之推”的困难在于,在家庭之外很难保证利益共轭关系(家庭的共同利益也并非绝对稳定)。墨子也看到了儒家的缺陷,因此想象了普遍之爱,所谓“兼爱”。兼爱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不靠谱,墨子并没有鼓吹无条件的兼爱,而是推销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之法”,他相信“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方案其实比儒家方案高明,但终究同样不可靠,它虽然不算错,但只是或然为真,而不是必然为真,因为爱人利人未必能够保证人皆从之(可以考虑搭便车问题)。看来,“家――国――天下”的传递性虽然是必要的,但恐怕不能依靠“道德之推”去解决。道德经不起利益的挑战,因此,“家――国――天下”的传递性很可能更需要一种经济学的解决。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或一种人际关系必须能够满足:(1)它的存在是每个成员的个人利益的共同必要条件;(2)其总体利益改进与每个成员的利益改进成正比,或者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挂钩一致。如果“家――国――天下”能够形成这样的经济学关系,大概就有望保证有效的传递性了。
无论天下体系还存在什么尚未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它仍然是一种最有潜力的政治理想。天下理念创造了最具和平气质和包容性的政治合作原则。天下体系的“无外原则”蕴含至少两个重要结果:(1)既然“天下”与“天”一样都是世界万民的公共利益和公共资源,天下理念就拒绝了把他者看做不共戴天的异己。这一点决定了天下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和”,即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谋求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2)既然世界多样性是天经地义,天下体系就拒绝单方面推广某种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从而剥夺其他观念和知识体系的生存空间。这是“礼不往教”的文化原则。《礼记》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别人自愿来学,与强加于人显然完全不同。
可以说,天下理念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制度想象:一个能够保证利益冲突最小化并且合作最大化的世界政治制度;一个能够承认并且维护文化权利的世界文化制度。这是天下理念最重要的遗产,也是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政治原则。
(摘自《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39.00元)
